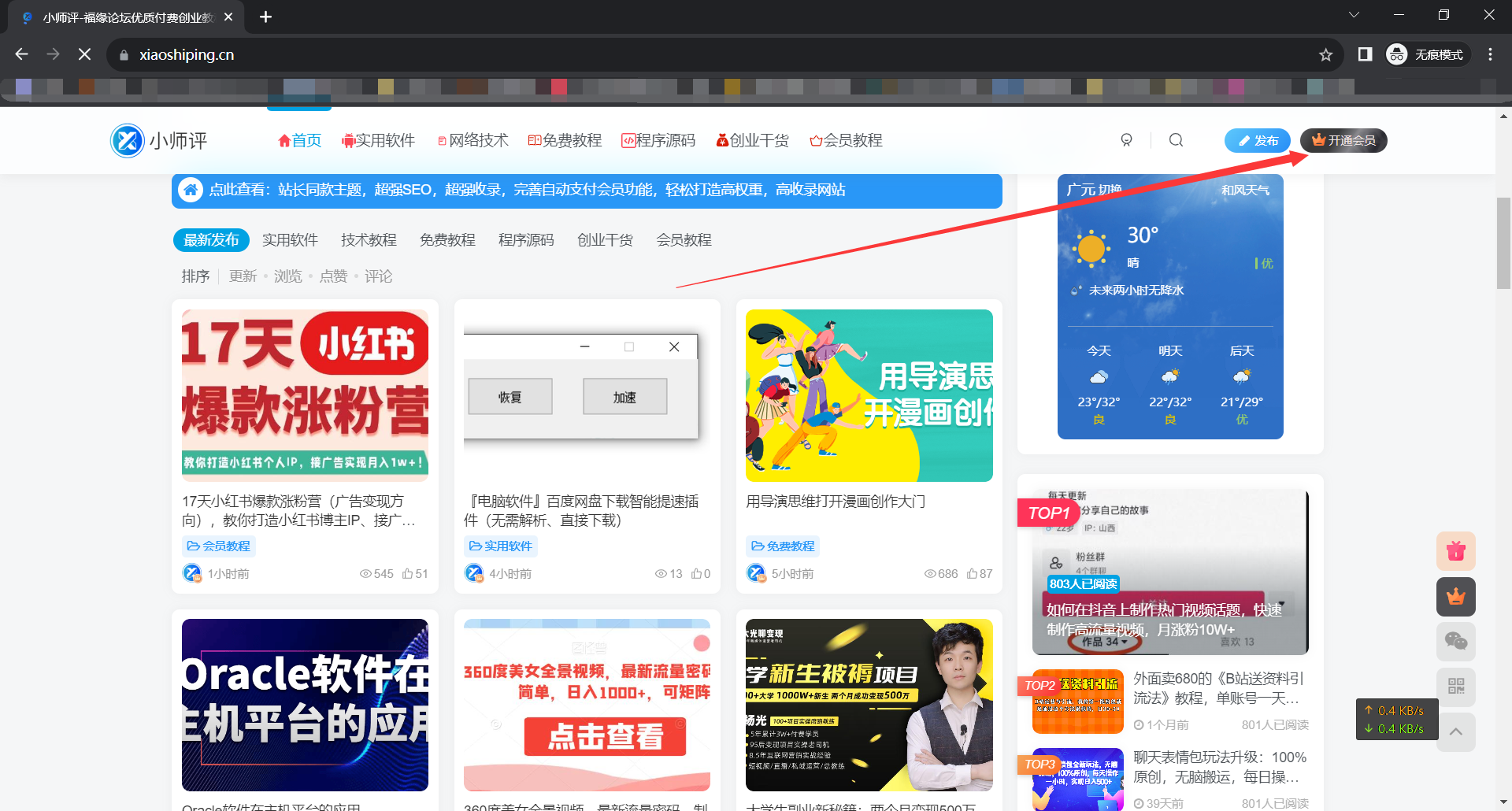![图片[1]-马尔克斯去世十周年:爱在瘟疫蔓延时,哪怕专制魔咒如影随形-小师评](https://img01.xiaoshiping.cn/xsp-bucket/2024/04/20240418044501171.jpg)
2年4月1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我当时在悼文中写道:
“在我记忆中,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二次死亡。”
第一次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我在某报上读过一篇关于书展的稿子,记者将马尔克斯写成“已故作家”。很显然,记者只是知道这个名字。
马尔克斯去世时,微博和朋友圈满屏都是悼念。也有几个真诚的朋友,坦言自己没读过《百年孤独》,或是压根没读下去。马尔克斯的晦涩,本就决定了他的作品不属于大众读物。他也未必在乎你是否读他的书,读不意味着高明,不读也不意味着失去了什么,但他肯定不喜欢有些人跟他装熟。
说起马尔克斯,很多人言必称《百年孤独》,我则独爱《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更喜欢它的台湾版译名——《爱在瘟疫蔓延时》。
港乐里也曾有一首《爱在瘟疫蔓延时》,那是周耀辉作为填词人的初试啼声,颇为惊艳。一句“不必亲近在这天,不想今后独溅泪”,俨然标准伤情歌,可是副歌部分的“独舞疲倦,倦看苍生也倦”,以及那句“静听天怨”,便让人听出了末世情结和大时代的悲怆。
马尔克斯的文学之路,同样与大时代息息相关,以至于他和一位好友常常被人相提并论。那是1948年的“波哥大事件”,那年4月9日,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自由派人士豪尔赫·盖坦被暗杀,首都波哥大陷入混乱,动乱导致数千人死亡。当时正在波哥大读大学的马尔克斯,从此对肮脏政治深恶痛绝,潜心文学。而当时正以学生代表身份在波哥大参加国际学联会议的另一位年轻人,却一心要“武装夺取政权”,他是卡斯特罗。
![图片[2]-马尔克斯去世十周年:爱在瘟疫蔓延时,哪怕专制魔咒如影随形-小师评](https://img01.xiaoshiping.cn/xsp-bucket/2024/04/20240418044503378.jpg)
暴力并未终止,1949年到1962年之间,哥伦比亚始终政局动荡,近三十万人丧生。此时的马尔克斯,坎坷困顿,一度流亡欧洲,他的《百年孤独》,要到数年后才开始创作并完成出版。1955年,他出版了《枯枝败叶》,1962年,他出版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它们必须要沾后来者《百年孤独》的光,在他成名后才成为经典。
拒绝政治的马尔克斯,无法在作品中回避政治。即使是并不魔幻现实,在技巧上极为传统的《爱在瘟疫蔓延时》,也在哥伦比亚的混乱背景下衍生剧情。那个海港城市喀他赫纳,在战争和霍乱中沉沦,仇杀与劫杀遍地。即使爱情无比热切,哪管天昏地暗,仍逃不开这乱世宿命。
这种大时代背景,使得那句人们熟知的“广告词”有些单薄,“他们在二十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八十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没错,故事真的是这样,但不仅仅是这样。
死亡与孤独,是与爱情并存的母题。在那个城市里,因为内战、霍乱和混乱的治安,到处都是腐臭的尸体。如果没有爱情,你还能从哪里获取勇气,在满目疮痍下生活?
但爱情本身,往往是最容易遭受阻挠的玩意儿。马尔克斯就借费尔米纳之口说:
“一个世纪以前,人们毁掉了我和这个可怜男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太年轻;现在,他们又想在我们身上故技重施,因为我们太老了。”
人们总是乐此不疲,毁掉别人的生活,然后,再毁掉一次。有时,他们甚至不需要借助战争,也不需要借助瘟疫。
霍乱曾真实发生,但它同样是一种意象,它的本质是孤独。人生而孤独,没有人能改变独个儿前行的命运。凄风冷雨中的仓皇,未必是每个人的肉体必经,却是灵魂不可逃避的路程。
霍乱还隐喻着爱情。爱情本就是一种病,疯狂的爱更如瘟疫蔓延。
所以,你必须相信,那个13岁的教会学校高傲女生,会与一个削瘦、近视的私生子电报员相爱。你更要相信,即使两人后来决裂了,可是在51年9个月又4天后,他会对新寡的她说:“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就是为了能再一次向您重申我对您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这样的爱情,不仅仅是瘟疫,也是一场两个人的灾难。
那年,他76岁,她72岁。他“鼓足勇气用指尖去摸她那干瘪的脖颈,像装有金属骨架一样的胸部,塌陷的臀部和老母鹿般的大腿……肩膀满是皱纹,乳房耷拉着;肋骨包在青蛙皮似的苍白而冰冷的皮肤里……”
在那漫长的等待里,他用了25本笔记本,记录了622场与污秽城市、持续瘟疫和无尽死亡并存的爱情。因为内心的期待,他最喜欢寡妇,直到老去。当她的手在他的下体“找到了那个手无寸铁的东西”时,他说“它死了”,还说“过多的爱和过少的爱都对它有害。”虽然,第二天,他能够以“迅速而可悲”的状态,完成与她数十年间的第一次做爱。他们错过了青春和美妙肉体,但也避过了琐碎生活的纷扰,直抵死亡。
在《爱在瘟疫蔓延时》、也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出版的十年前,马尔克斯还写出了《家长的没落》。在他看来,这部构思十余年,并花费七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是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仅次于《百年孤独》的重要作品。
作为一个伟大作家,即使他远离政治,也不可能避开那个世纪里困扰人类的魔咒——专制。
![图片[3]-马尔克斯去世十周年:爱在瘟疫蔓延时,哪怕专制魔咒如影随形-小师评](https://img01.xiaoshiping.cn/xsp-bucket/2024/04/20240418044505239.jpg)
与《百年孤独》的隐喻不同,更与《爱在瘟疫蔓延时》隐藏于爱情之后的暗流不同,《家长的没落》的故事直接以独裁者为主角。
它有点魔幻,有些情节还很夸张。它有散文诗的风格,却像一个寓言。那位大独裁者、某国总统尼卡诺尔,推行高压统治,大搞情报网,以暴力镇压为手段,大肆捕杀政敌和反抗者,甚至干脆宣布国家进入瘟疫状态,授意军队随意屠杀民众。他情妇无数,孩子有几千个,连刚出生的儿子都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出卖主权,将国家的专利权和铁路航运权都让给了外国人……他对自己的第一夫人言听计从,但有一天夫人被猎狗吃掉,他为此杀人无数,而趁机将近千人诬为“仇敌”并将之杀掉的德拉巴拉,则成了他的心腹。
我不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马尔克斯如何看待世纪魔咒,但就在1958年底古巴革命时,他一度倾向左翼,并与卡斯特罗成为好友。《家长的没落》出版后,世界文坛为之轰动,认为这部作品“无论从结构还是语言来看,在拉美文学界以及作家本人的作品中,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对于拉美人来说,这部小说尽管魔幻,却处处可以找到原型。在那个一度无比混乱的大陆上,有太多这样的独裁者。比如宣布死讯又突然复活的“桥段”,便曾真实发生。但作为寓言存在的它,足以全面影射上世纪摧残半数以上人类的魔咒。
但对于马尔克斯来说,政治从来都不是其作品的唯一母题。他自己也曾说过,除了政治的肮脏,他还想表达人类在这肮脏中的艰难困顿,自我挣扎。早在他创作《枯枝败叶》时,他就强调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偏偏在那个时代,哥伦比亚政治动荡,民不聊生,他的观点很容易引起朋友们的抨击,责难他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
只是,喊口号容易,甚至一辈子喊口号都很容易,可始终悲悯地看待这个世界,却非大师不能。马尔克斯从来都不是某些在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国内学者所鼓吹的那样,是什么“阶级分明的作家”,他只是坚持探寻人类的本质——孤独。
那些乱世中的孤独、爱情中的孤独,还有不被时间所改变的百年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