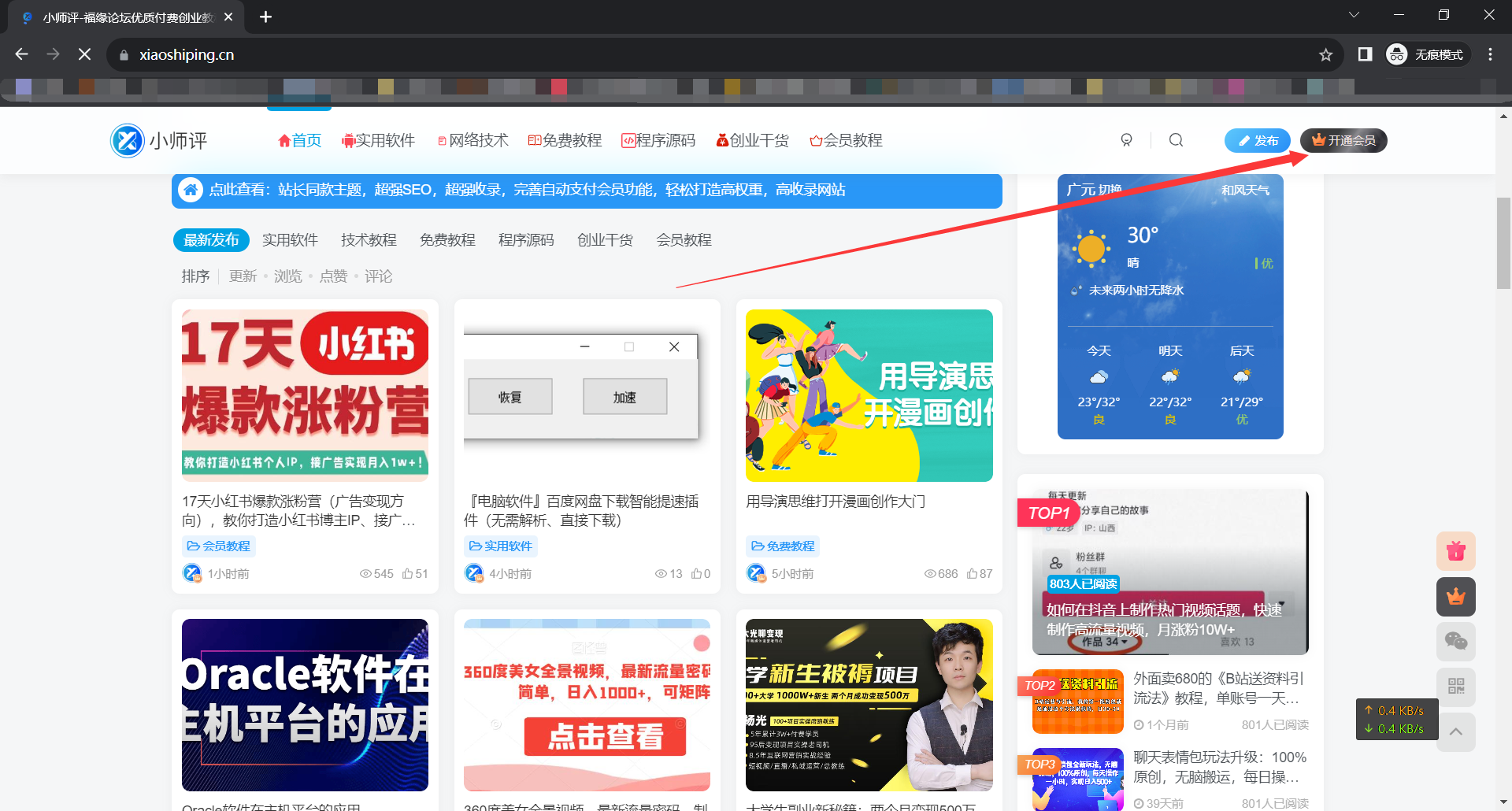最近,我看到社交平台上有人讨论 ” 怎么样才能实现游戏自由 “。最初问这个问题的人,是这么说的:” 非常非常想玩游戏 …… 想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不用担心该学的东西没学、该读的论文还没看、该做的工作还没做,想要玩游戏,要有时间,要有配置不错的电脑,要有空间来安置它,想玩联机游戏的话还需要一个能说话的自己的空间。但拥有这些的前提是能赚钱,而赚钱就意味着没有时间。”
![图片[1]-游戏和乡土文学-小师评](https://img01.xiaoshiping.cn/xsp-bucket/2024/07/20240701024336621.jpg)
图 / 小罗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诸多讨论里,有这么一个情绪化的回复:” 这说明你并不爱游戏。”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有那么一丝发泄的意思——你想做个符合社会期待的人,那好,你没时间玩游戏就是活该。
” 游戏 ” 在这样的语境下,成了一种反传统、反压抑的代名词,和 10 年前没什么不同,但在这次的讨论中,还加上了一层 ” 自发 ” 的意思——讨论者们并不是被某个具体的力量或者权威阻止玩游戏,而认为自己 ” 没有时间玩 “,被生活的压力压抑住了。
但他们对游戏的欲望,却又随着这种 ” 压抑 ” 成倍增加。最后,游戏的意义似乎越来越大,就像有些讨论里说的,” 游戏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在压力最大时,也坚持玩游戏,你不爱游戏,所以你没法放弃一切,拼命地玩,你在这抱怨,就说明游戏和你没关系 “。
对这些 ” 最爱游戏 ” 的玩家来说,他们的爱,在享受游戏本身的乐趣外,似乎又多少混杂了逃避现实或者更深的东西:一遍遍地打着那几个老游戏,一场场地踢球,一局局地对枪,一次次的下本,这是对游戏的爱吗?我不确定。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了乡土文学——奇怪,我怎么会想到这个?中学时,我读了很多讲地方的小说,比如汪曾祺的《大淖纪事》。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地方写作,是一种对主流写作的疏离,” 地方 ” 对抗的是 ” 中心 “,它是或隐或显的、对想象的中心的对照或者对抗。
后来,许多主流奖项都向着写地方的小说靠拢。长大一些后,我就不爱看这种小说了,我觉得它们的人物很脸谱化,尽管总是写生态史、生活史、文化史、底层史,但我从中见不到足够多有着各种各样 ” 文学典型性 ” 的人,也没有什么创造力和想象力,而是文化、历史等直接对抗意义上的 ” 压抑和反抗的写作 “。但这种解构宏大叙事的、对抗压抑的写作,本身同样成了一种压抑。
在我看来,很多语境下,玩家对玩游戏的看法,和主流视角对乡土文学的看法似乎是一样的:解构传统社会规范的、用来对抗压抑的 ” 玩游戏 “,本身好像也是一种压抑,一种全然不顾现实的逃避,和这种逃避相对的,就是抱怨自己 ” 没时间玩游戏,一点不自由 ” 的人们。在讨论中,玩家们自发地分成两个极端,无论是哪个极端,似乎都离 ” 用正常心看待游戏、玩游戏 ” 越来越远。
我觉得,无论哪种极端,都是不自由的,没有时间固然是一种不自由,但若怀着逃避的心态玩游戏,似乎也称不上自由,更不用说爱了——或者说,仅仅玩几个游戏,需要去如此热烈地宣告自己 ” 爱 ” 它吗?
游戏就只是游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