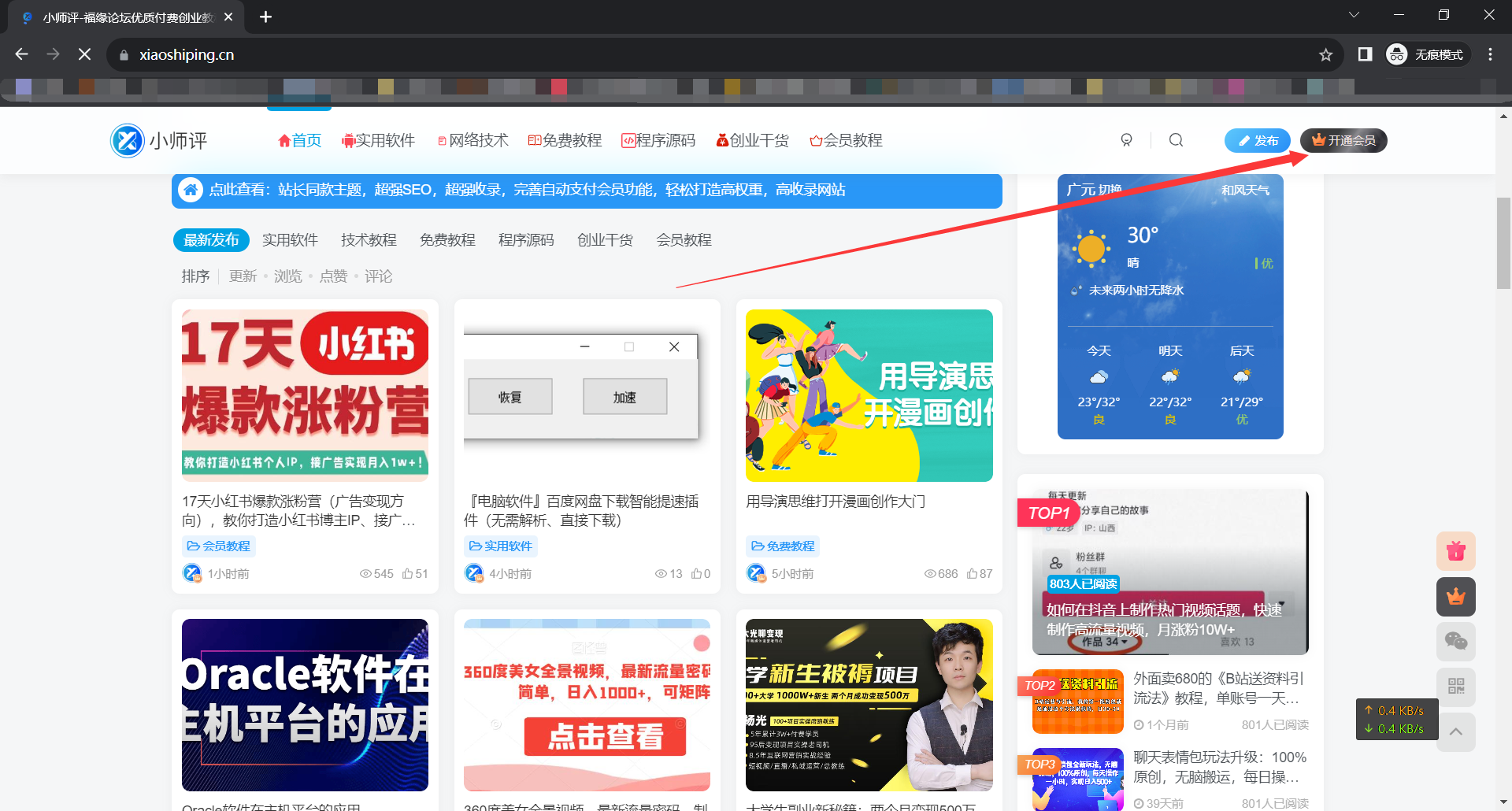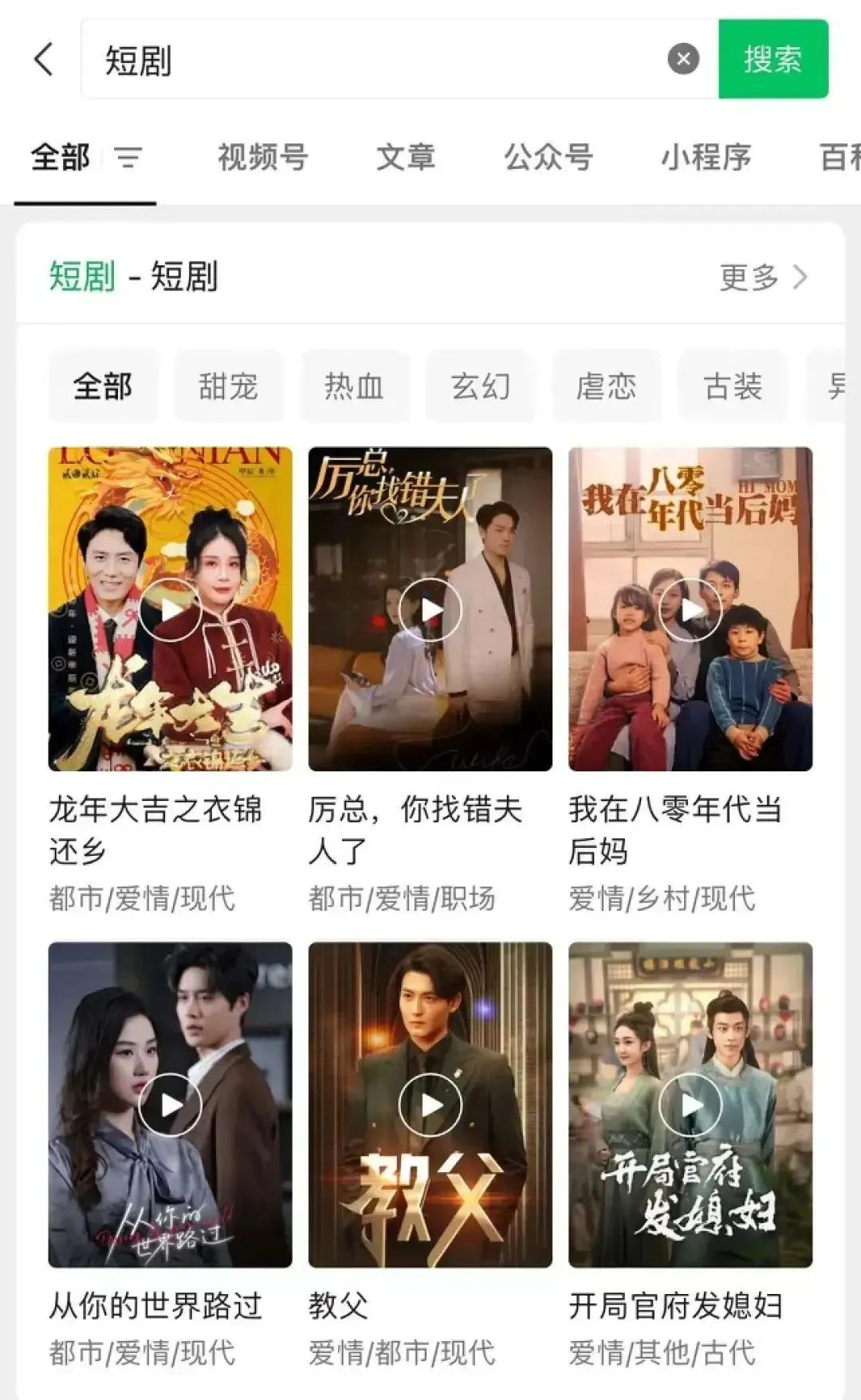“有时候,真的希望孩子能走在我前面。”一个男人的这番话,令韩龙有种浑身触电的痛感。他们同命相怜,都是孤独症孩子的父亲。
四年前的一天,韩龙两口子把儿子图图带到了医院。“孤独症”三个字,就像三根刺狠狠扎进了他们的心里。
孤独症病理不清,这是一场无法归因的苦难。孤独症无法治愈,这是一场终点不明的苦行。怎么干预治疗?到哪里上学?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生存?每天睁开眼,为孩子操心的事一件件扑面袭来。两代大人疲于奔命,不再有自己的生活。
全国有200多万个孤独症儿童,牵连着200多万个家庭。在这场苦行中,痛苦和绝望缠绕,把大人们的心力、体力、财力一点点耗尽。有人崩溃、有人麻木、有人选择放弃,不少家庭因此而破碎。
也有人接纳命运,决定与苦难共舞,韩龙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想做点什么,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也为了200多万个同命的家庭。一年之内,他先后推开了两扇门,阳光照了进来。
韩龙和妻子欣欣的工作都很忙,累了一整天回到家,他们想跟三岁的儿子亲昵。但他眼神躲闪,也没什么表情,总是如此。儿子长了一双有福气的大耳朵,像极了国产动画形象“大耳朵图图”,他们就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图图”。
那是四年前的事,两人初为父母,第一次养娃。孩子一天天长大,能走能跑,喜欢托马斯小火车;虽然发音含糊,但比其他孩子更早开口说话。“也许情感上发育迟缓了点?”对于图图不太亲近他们,欣欣当时这样理解,没多想。
姥姥日常照顾图图,她最先觉得不对劲。小区里同样大的孩子,今天学会了跳绳,明天学会了打鼓,只有图图,无论怎么教,都“油盐不进”。一次节假日,有个亲戚过来,带图图出去玩。她发现,图图不听指令,没有安全意识,就委婉地暗示两口子:是不是该带去医院检查一下?
两口子慌了,打开手机搜,跳出“自闭症”。再看症状:刻板行为、兴趣狭窄、精细运动能力差……很多都对得上。他们赶紧预约挂号,到医院后填量表,面诊。诊断书出来了,上面写着“ASD倾向”。
图图的诊断书。
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坍塌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的孩子?”他们不停地追问。欣欣难以接受,用自我麻痹的方式对抗这个沉重的打击。她拒绝交流,拒绝看一切跟孤独症相关的信息。很多次,家里没人的时候,她情绪崩溃,一个人哭得歇斯底里。
韩龙同样坠入了绝望的边缘。他说,如果是其他身体疾病,至少知道怎么治疗,花几十万几百万,治疗效果总归有个大概。可是孤独症不一样,它找不到病因,要终身干预,看不到希望,几乎是条不归路。
ASD,全称“孤独症谱系障碍”,也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自闭症,更准确的名称是“孤独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神经系统发育障碍,相关脑部变化在胎儿时期就已经发生。有这种障碍的孩子,通常会在3岁之前就出现明显的行为异常。根据DSM-5诊断标准,他们有两个主要的表现特点,一是“社交沟通障碍”,二是“重复、局限的行为及兴趣爱好”。
不同孩子有显著差异,这也是为什么图图最初“误导”了大人。他并不内向孤僻,相反,他很早就学会了说话,并且喜欢说话。他会不停地问问题,甚至明知故问,似乎很享受这个过程。
后来他们才意识到,这些交流是有问题的。图图大部分的语言,要么表达饿了渴了这些基本需求,要么更像在自言自语。有来有回有感情的高质量交流,很少很少。
影视剧爱把孤独症人群塑造成“孤独的天才”,渲染他们具备某种异于常人的天赋,这是巨大的误解。实际上,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大约一半还伴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正常生活。
2020年《神经科学通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儿童中ASD流行率约为0.7%,保守估计孤独症儿童总数超过200万。孤独症儿童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和其他人隔着距离,因此被称为“星星的孩子”,简称“星宝”。200多万个星宝的背后,是200多万个星宝家庭,他们有着同样的追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的孩子?”
满世界地打听治疗、康复机构,全天候的陪伴,一纸诊断书改变了全家人的生活。老人始终无法接受现实,韩龙和欣欣一边强撑着,一边艰难而缓慢地接受现实。韩龙率先振作了起来:“再多一点负能量,这个家就要被压垮了。”
6岁之前是孤独症的黄金干预期,图图当时3岁多,耽误不得。姥姥期盼着出现奇迹,韩龙和欣欣学习相关知识后,理性地调低了预期:希望能通过干预,帮助图图融入社会生活。
公立医院大多只作诊断,孤独症儿童确诊后,通常得到商业康复机构接受干预。如果孩子状况不错,还可以设法送到融合幼儿园。这类幼儿园一般由园方和特殊教育机构合作,里面既有健全儿童,也有各类障碍儿童,创造一个平等、尊重、互助的融合教育环境。
韩龙和欣欣一边搜集信息、学习知识,一边为图图寻找合适的去处。姥姥全然投入,每天接送、照护。从康复机构到融合幼儿园,辗转北京、天津、青岛,一家人一次次地搬家,只为给图图找到最理想的归宿。这个过程远比之前设想的复杂、艰辛。
挑选康复机构,要考察老师的办学资质、教育理念、训练方式等等。韩龙发现,机构老师流动性很大,有的才过两三个月就换人。孤独症孩子重新适应一个陌生老师,谈何容易?
有家融合幼儿园,环境、师资都很好,但欣欣很快发现,园方在普教和特教的融合支持上有点割裂。好几次家长开放日活动,老师都不希望她到校参加。“可能不想让别的家长知道,园里还有孤独症孩子。”欣欣推测。
欣欣最终找到了一家特别的幼儿园,园长的孩子也是孤独症儿童,所有老师都有特教资质,包容和支持的环境很不错。但问题是,报名入读的孩子逐年减少,融合教育资源投入高昂,这让幼儿园举步维艰。
更沉重的话题是“钱”,星宝家庭通常要把全家一半的收入花在孩子身上。开支主要包括学费、干预费,以及针对弱项的课外补习费。图图在上的补习课包括:社交、精细运动、注意力训练、感统训练等。对于绝大多数星宝家庭来说,经济压力无法承受。
除了钱,还需要陪伴。主流观点认为,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坚持长期高强度训练,干预效果更佳。因此,在机构干预之外,家长们需要亲身投入。他们争分夺秒,拼命抓紧6岁前黄金期的每一天,即便孩子在玩耍休息的时候,也总想着能教他点什么。
韩龙在陪图图读绘本。亲子陪伴和绘本阅读对孩子的康复有帮助。
欣欣面临两难的选择。为了孩子,她可能需要辞职,但这样一来家里就少了一大块收入,无法继续给图图购买资源,很多机构服务都得放弃。权衡再三,她决定继续上班,姥姥接过了更重的担子。
图图曾在姥姥的陪伴下远赴青岛,入读当地一家专业的孤独症康复学校。这所康复学校全国知名,吸引了各地的星宝家庭。每月基础学费七八千元,要求一位家长全天陪读。大部分家庭都不得不安排妈妈辞职,在附近租房带孩子,爸爸工作赚钱负责“月供”。支出是固定的,收效却因人而异。漂泊异乡,经济和精神压力巨大,很多家长难以承受,无奈带着孩子中途退学。
孩子长到6岁以后,家长们其实也不可能就此停止干预,这将贯穿他们的一生。韩龙和欣欣白天上班,下班后陪伴图图,孩子睡着了以后,还要抽空看专业书,学习康复知识。“久病成医”,他们成了这个领域的半个专家。
图图今年7岁多,确诊4年了,姥姥始终没能接受这个事实。女儿女婿一遍遍地劝慰她:“图图智力测试得分只有70,以后能正常生活就好。我们图图没法像大多数人一样,走读书-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的路线,他会走出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但姥姥还是相信:孩子总有一天会变好的,会变成大家认知中的正常孩子。
姥姥每天接送图图,每天都在受挫。长期的负反馈,让她的焦虑情绪越来越严重。欣欣看着着急,想给妈妈找个心理医生,或者干脆咬咬牙自己辞职,让妈妈从“一线”退下来,但经济压力又不允许。
韩龙是阿里巴巴的工程师,欣欣在一家地产公司工作,两人收入都还可以,家里老人还能出大力、帮大忙。他们家尚且焦虑,更多星宝家庭的处境可想而知。韩龙和欣欣加入了星宝家庭社群,看到了太多在重压之下艰难前行的家庭。
以孩子确诊为拐点,星宝家庭的命运断裂成截然不同的两段。有的家庭难以负担费用,父辈祖辈两代人打工赚钱,6个钱包撑起一个孩子。很多夫妻因此感情破裂离婚,女方独自带着孩子苦熬。
星宝家庭不敢想太远的事情。有个星宝爸爸对韩龙说:“有时候,真的希望孩子能走在我前面。”韩龙听后,有种浑身触电的痛感。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他想为大家做点什么,“也是为自己的孩子积德”。
星宝家长们每天都在付出,得到外部的理解和支持不多,久而久之,能量逐渐耗尽,陷入精神危机。韩龙觉得,如果能把大家聚到一起,互相激发、互相赋能,帮大家疏通情绪郁结,应该是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作为阿里员工,韩龙首先想到寻求阿里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他在公司内网搜到负责人的名片,直接打电话过去。负责人很快就被他的想法打动了,支持他办线下活动。就这样,韩龙发起了“星星加油站”公益幸福团,引入专业志愿者,专为星宝家庭加油打气。
越来越多的星宝家庭和志愿者参与了进来。家长们互相倾诉、彼此鼓励。在这个社群里,健全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结伴看展、做游戏,在接纳与尊重的氛围里,韩龙看到了他理想中的未来图景:“如果图图未来能生活在这样的关爱环境里,我们也就放心了。”
目前,这个“幸福团”已经在上海和杭州成立了分团,总共办了40多场活动,覆盖超过500个星宝家庭。去年3月,韩龙站上了阿里公益晚会的舞台,向同事们讲述星宝家庭的困境、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以及“幸福团”正在做的事。
韩龙PPT的第一页,是一张自己牵着图图走路的照片,那时候图图才3岁,走路跌跌撞撞。PPT的最后一页,是图图独自行走的背影,他长到了7岁,个子高了不少。韩龙说,这首尾两张照片是一组隐喻:星宝小时候,大人带他们往前走,但总有一天,他们要独立面对这个世界。希望到那个时候,孩子有足够的能力,社会也有足够包容的环境。
韩龙牵着图图的背影。那一年,图图3岁。
韩龙的讲述,让会场陷入了沉寂。观众席上,不少同事已经抑制不住泪水,有的甚至泣不成声。
韩龙的那次登台分享,让星宝话题在阿里内部“出了圈”。“他们太苦太难了,听得我当场就泪奔了。”当时在场的95后姑娘放放回忆。在这家超大型互联网公司内部,一些人开始思考:我们能为星宝家庭做点什么?
AI成了最多人想到的解法。去年,AI成为行业新趋势,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实验室里的技术加速转化为上手可用的产品。有人找到韩龙,讨论如何把新技术利用起来。大家一致认为,AI和儿童绘本的结合,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突破口。
绘本是儿童读物的重要品类,很多孩子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都是从读绘本开始的。李晨亮是阿里巴巴通义实验室的算法工程师,也是一个2岁小男孩的爸爸,他对此深有感触。
李晨亮挑选绘本很用心,经常买回家陪儿子一起读。有一天,他听儿子在背《咏鹅》,就给他买了本可以点读的《唐诗三百首》。三个月后,儿子会背将近50首,让他喜出望外。近段时间,李晨亮发现儿子会动手打人,就买了本《手不是用来打人的》。儿子看得津津有味,行为也明显有了变化。
对绘本有切身的体感,又想为星宝家庭做点事,所以当韩龙和几个热心同事找到李晨亮时,他毫不犹豫就答应加入,担任这个公益项目的技术主力。他很快意识到,星宝比健全孩子更需要绘本,而且,他们需要不一样的绘本。
韩龙耐心地给项目组介绍孤独症儿童有何不同,提了许多具体需求。比如,普通孩子通常喜欢丰富的色彩,但对星宝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混乱无序。一些绘本图文并茂,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和俏皮话,星宝却不喜欢这样。弯弯绕绕会让他们一头雾水,他们也不会觉得俏皮话多有趣。简洁的画面,和直白的文本——这是他们需要的。
“个性化要求太高了。有的星宝不能看到芒果,有的星宝不能看到波点。星宝家长很难找到特别适配自己孩子的绘本。”项目组成员张好介绍。
这同时也是特教老师的痛点。陶焘是“海豚乐乐”儿童发展中心的一名孤独症儿童康复干预师,有丰富的干预经验。陶焘介绍,很多星宝会优先接受“视觉提示”,用图片、绘本来辅助理解,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干预方式。
在“海豚乐乐”机构的各个生活场景里,如卫生间、洗手台、门口,都贴着具有“视觉提示”功能的图片。对于缺乏情景想象能力的星宝来说,这些图片就像使用说明书,帮助他们理解和掌握各个场景中必备的生活技能。
模拟不同场景的绘本,是陶焘每天频繁使用的教学工具。但由于星宝之间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多数时间他都无法直接找到合适的绘本,只好花大量时间“手作”。如何高效地实现定制化,是陶焘也在钻研的问题。在得知韩龙、李晨亮们发起的项目后,“海豚乐乐”积极加入其中。
大家从不同的视角,把林林总总的痛点列出来,和AI的能力一比对,方向变得清晰:为星宝家庭、特教老师研发一款可定制、个性化的AI绘本工具。大家积极“摇人”,组建了一个近20人的志愿者团队,在线协同启动开发。
浙江工业大学王永固教授加入了进来,他投身特殊教育信息化事业多年,担任专家顾问。阿里旗下AI模型开源社区“魔搭”的开发者吕昭波加入了进来,他是一个活跃的AI应用开发工程师,担任产品经理。
吕昭波有两个儿子,孩子睡觉前爱听他讲故事,但他自认为不会讲故事,“不知道怎么开头,也不知道怎么收尾”。这时候,他“工科直男”的优势显出来了,他干脆开发了一款儿童故事AI产品。产品很讨孩子喜欢,通过它,孩子可以跟动画片里的角色进行语音互动。
这款产品让吕昭波与AI绘本工具开发团队结下了缘分。当魔搭社区的运营负责人周洁琪顺藤摸瓜向他求助时,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深入了解孤独症家庭的状况后,深受触动。“大家同样为人父母,心是相通的。我很想尽自己的能力帮把手。”他说。
志愿者们分处全国各地,分文不取,白天做本职工作,下班后切换频道,参与研发AI绘本工具。人在上海的吕昭波把麦当劳开辟为“第二战场”,下班后就过去“加班”。每周二、周四的晚上,他会组织大家在线开一个多小时的会,讨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项目进展。
产品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星宝和星宝家庭增进理解的过程。吕昭波举例说:“有些孤独症小朋友看到桥会难受。因为他想的是,那么多人在这座桥上走,桥会不会很累?如果桥面上有一点裂痕,桥会不会很痛?”
大家给产品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追星星的AI”。“星星”代表星宝群体,AI要主动去追星宝,而不是让星宝去追AI。“人有温度,AI才有温度。这是我们对这款产品的思考。”项目组成员张好介绍。
经过2个月时间的开发,“追星星的AI”终于做成了。在特殊教育专家的指导下,产品技术团队以阿里巴巴“通义”系列大模型为底座,基于专业实践和学术验证的原则,对模型进行了针对性的微调优化。通义APP为“追星星的AI”开设了专门的频道,打开页面,只需输入一句指令,就能生成一个绘本故事。
“追星星的AI”的产品页面。
比如输入指令“用一个小故事告诉小朋友在公共场合要保持安静”,然后设置篇幅和主角性别,以及避免出现的内容。AI很快就自动生成了一篇图文并茂的绘本故事,并能自动朗读。目前,“追星星的AI”可以生成常识认知、社交礼仪、心智解读、趣味故事4类内容,并可设置3个层级的认知水平。
在这2个月的时间里,惊喜不断。首先是韩龙一家,他们儿子的小名取自国产漫画《大耳朵图图》。在志愿者的撮合下,大耳朵图图的“家长”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带着“图图”参与了进来。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彭勇介绍,为了增加趣味性,该厂授权“追星星的AI”使用其旗下经典动画形象,星宝家长可以使用以他们为主角的模板,给孩子讲故事。
产品6月15日上线后,也立刻获得了苹果应用市场精选栏目推荐。“用AI关照更多弱势群体,这个行业共识正在形成。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科技公司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参与进来。”吕昭波说。
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参会者在阿里巴巴展台体验“追星星的AI”。
在“追星星的AI”面世之前,欣欣就试过使用AI大模型工具给图图生成故事。但这些工具都以健全孩子为目标用户,生成的内容并不符合图图接收信息的习惯。现在,她多了一个适配图图的陪伴工具。“如果因为这个AI工具,星爸星妈们每天能腾出半个小时的时间透口气,也是极有价值的。”韩龙这样认为。
韩龙说,最终目标还是要促成星宝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社会的宽容和接纳是大前提,基于这个大前提,在干预、陪伴、监护等方面,AI技术未来或许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在“追星星的AI”公益短片的跟帖区,有位江苏的网友留言:“科技的力量!我们总是要求星宝融入普通环境,强行让他们遵守所谓的‘规则’。事实上,‘进入他们的世界’才是对他们的爱和尊重。”